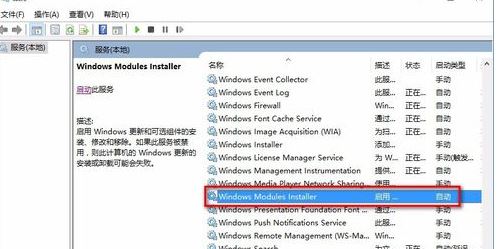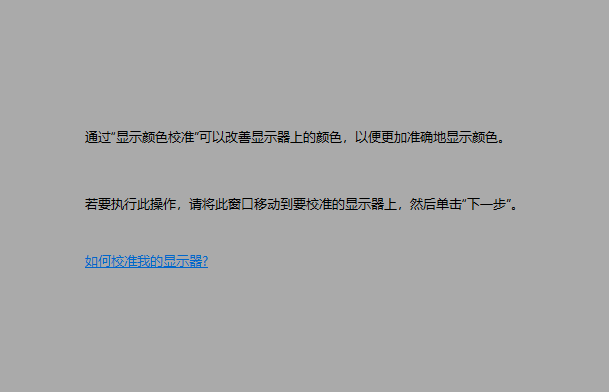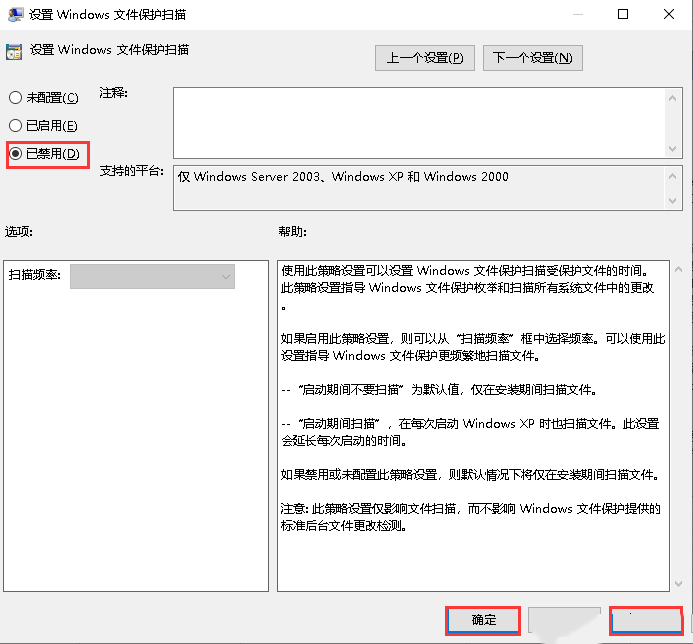在文字中与杨苡重逢,触摸历史的感性
我展开一幅历史画卷,犹如展开一匹过长过长的陈旧锦缎,虽曾有过光彩夺目之时,却早已千疮百孔,斑驳灰暗,乃至一撕即破。有几处已脆薄如纸,翻开时如林中枯叶,微风轻拂叶便飒飒作响,仿佛抗议说:‘碰不得!’也有的仍能看得出当年的姹紫嫣红,令人迷恋,如月下一股激流自山涧冲下,还能听到它欢快呼啸之声。”1980年代末,杨苡一篇回忆沈从文的文章中这样展开她的历史画卷。杨苡似乎特别喜欢“呼啸”这个词。

1953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杨苡突然就想起了她正在翻译的《WutheringHeights》中约克郡旷野的那所古宅。“呼啸山庄”这四个大字兴奋地从她的笔尖跳跃到了纸上。
此后,这部小说虽有多个译本,但不同的译者均选择了“呼啸山庄”这个书名。
这是向经典致敬。这位和“五四”同时代的著名译者,值得这样的致敬。遗憾的是,她的人生不再呼啸,属于她的或美丽、或斑驳灰暗的画卷止于50天前的1月27日。
所幸的是,就在杨苡去世前,《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出版,今天,我们在文字中与杨苡重逢。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杨苡的人生也是时代本身
作为译者,作为隐身于名著背后的人,杨苡更广泛地为人所知,很可能是2021年5月底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
这部评分颇高的影片,片头过后的黑暗中,伴着风铃传来的第一个声音便是杨苡的——“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我的父亲是1919年去世的,就是我生下来那年去世的。可以说我生下来我还是穿孝的。”
这段话说完,屏幕亮了起来,一个宅院进去,一边是开着的蝴蝶兰,一边是轻摇着的风铃的门里边,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排布玩偶和两幅画,接着是一张框起来的黑白相片。相片上那个英俊的青年,是著名翻译家和诗人、《红楼梦》英文版译者杨宪益先生。
画外音同时响起:“我八岁到十八岁,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对我哥哥崇拜,绝对崇拜。到现在,谁也不能跟我哥哥比。”接着,错落摆着的几排黑白相片过后,画外音在继续:“我崇拜的人,除了我哥哥,当然就是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哥哥,那个是我的暗恋。”
这段话说完,满头银发的杨苡才出现在镜头中。“我是十七岁认识巴金的,巴金的《家》跟我们家很像很像。”
不是很了解杨苡的人,在没看完《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之前,只听杨苡在《九零后》中所说,是不会知道她家和巴金的《家》到底像到什么程度,更不会知道杨苡这么说,有多谦虚、多低调。
1919年,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这个大家族的祖籍是安徽泗州,祖上有四个晚清的翰林、两个总督,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中国银行行长。清末民初,甚至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天津一带,只要一提起安徽泗州的杨家,不少人都会连声称道、肃然起敬。
到杨苡这一代,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她和她的丈夫赵瑞蕻都是著名翻译家。她翻译的代表作是《呼啸山庄》,赵瑞蕻的翻译代表作是《红与黑》。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杨苡曾如是说。其口述整理和撰写者、南京大学文学院余斌教授惊讶过杨苡讲述往事时良好的画面感,可想而知,她这么述说的时候,有多少人和事在她的脑海里呼啸而过——沈从文、巴金、闻一多、吴宓、穆旦等等,历史的天空里,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人都曾真真切切地重现在她的面前。某种程度上说,时代既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也是时代本身,至少,是时代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切片。
她讲述的重点都落在“无关宏旨”处
杨苡出生和成长于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的时期,也正是新文化和相对应的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时段。这个时段的青年,既热心国家和民族兴亡的大事,也积极审视所处的家庭及自身。巴金的《家》的出现以及《家》在当时的影响即是一个例证,无论是否革命青年,都向往冲出家庭的牢笼。
“过去的大家庭生活,规矩特别大,特别多。讲规矩,其实就是讲等级。正室和侧室,差的不是一点点,尊卑绝对分明。”杨苡的母亲,正是所谓侧室,虽然她家贵为正室的“娘”已经够善良,但旧家庭正室侧室的设定,便注定了“娘”必然要充当恶人的角色——和杨苡同母的哥哥杨宪益刚一出生,便被抱到正室且没生养出儿子的“娘”的怀里。这样的家庭结构,即使再大再富裕,一旦有渲染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新风吹入,目睹过不平且还没被旧思想完全占据头脑的年轻人就容易觉醒乃至成为一切旧模式的控诉者和掘墓人。
杨苡直言她对她家的印象很糟糕,“鸦片、小脚、姨太太,让人气闷的生活方式……要用标签的话,这不就是标准的封建家庭嘛。”厌恶之情扑面而来。她坦言,年轻时候最强烈的冲动,便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摆脱那个环境,到外面广大世界去。
“他老是叫我忍耐,所以我就是也很生气,你们可以出走,怎么我就得忍耐?”《九零后》中,即使时过境迁,杨苡还是心有不平。叫杨苡忍耐的人,有她的精神偶像巴金。在其口述自传里,她回忆说曾在信中跟巴金说了要做其笔下的觉慧,但巴金回信说她年纪太小,应该要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杨苡最后能够离开家、离开母亲身边去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并不是其生气或反抗的结果,而是因为她写的一首诗被认为是“抗日”的,出于对杨苡安全的考虑,杨宪益给母亲写信,说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去,后果不堪设想。
到昆明后,杨苡便向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投稿,跟穆木天、罗铁鹰等诗人一起开座谈会,吃小馆子。这是她在天津不可想象的,在天津,家里不让她和她的朋友那样去游行和参加集会,但到了昆明,她可以“我行我素”,有了一种成了大人的感觉。
“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杨士骧、杨士琦在清末政坛上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整理和撰写杨苡口述自传的余斌教授特别喜欢的,便是杨苡先生全然私人化的角度。这是一个不同于正史的角度,同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因而有了不同的呈现。
萧珊去世之后,杨苡收到了她们共同的好友穆旦写来的信,信中说“好友一个个死后,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杨苡没有让自己成为谜,她的口述自传透明清澈,如月下激流,深情款款绕经了山河故人,终呼啸而去。
传递出了“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3月1日,南京的世界文学客厅,追思杨苡先生的活动“在文字中与杨苡重逢”现场,和杨苡先生有着10年长谈与倾听的余斌教授有些“出戏”地想象过假如杨苡先生来到了追思现场。
“以一位长辈、一位祖母的身份,此时此刻,她会说什么呢?”余斌想。余斌认为她对新得到的诸如“名门闺秀”“最后的名媛”“翻译大家”之类的标签发表意见,如果是在家中,她会很鄙夷地说:“又是炒作!”且多半还会加上两个字:“恶心!”但,假如在追思现场,她会注意到说话行事的“得体”,不会说“恶心”,但会表现出不屑。
余斌这样的假想,基于他十余年倾听杨苡所形成的了解。
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余斌教授,本科便是在南京大学读的。读本科时余斌修过赵瑞蕻先生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余斌和杨苡先生的认识,是他留校任教之后,他听说杨苡先生想看他撰写的《张爱玲传》,便赶紧登门送书。第一次登门,他们便聊了两个小时左右。
余斌喜欢和杨苡先生闲聊,“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肖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里遍布这样的“掌故逸事”或者说时代整体氛围的“细枝末节”。
“口述以其‘文体’的特性,必是叙事为主轴的,不仅注定盖过其他,甚至几可与叙事画等号,那么,口述作为‘野史’,正可补文章的‘正史’之阙。即使所写所述是相同的人与事,出现在文章与口述中,也会有微妙的差别,其不同也许不在于内容的出入,而在角度与口吻上的异趣。两相参看,庶几‘全貌’。”余斌认为口述是可以补正史之阙的,但杨苡先生一直对其口述是否有价值将信将疑,曾多次问他出这么一本书值不值,他花这么多时间后不后悔。基于自己对口述史价值的认识,每次,他都很坚定地回答:“值,肯定值!”
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的后记中,余斌坦言,他更感兴趣的,恰恰是杨苡先生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私密情事是这部口述自传中体现“普遍的人生的回声”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值得一看。讲述者的语气措辞,不见一丝今日吃瓜八卦的样子,读者也就感觉不到一丝低俗,相反,对人生、人性的无奈与多样,或会增添新的认识。
对谈 “触摸历史需要很多感性的东西”
潇湘晨报:非常感谢您能够整理出这么一部能够看到百年中国生动细节的口述实录,虽然,它只是一部个人的口述史。
余斌:希望它是这样,希望能有这个效果。从我想要做口述史的时候,其实我最看重的杨先生的记忆力的特点,还有它的特别多的这个细节,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所以我也是尽量把这些细节给呈现出来,希望这些细节本身就可以传递信息,而且是不是那种线性的,是比较丰富的信息。
杨先生记忆力非常强,但是她自己未必认为这些细节有多大的意义,我一直向她保证说这些肯定是有价值的。
例如,她跟我讲她读书的中西女校。中西女校就是一个教会女校,它的具体情形,包括它的位置,周围是一个什么环境,我听了都很有意思。那个学校不是在租界,而是在和它周围的环境有很明显区隔的地方,她每天上学怎么走这个路,这些我都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包括学校里面男教师女教师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读者对这些是也会感兴趣的。读者看到这些信息,对历史、对过去的事情,会更有一种可感性。老是讲触摸历史、触摸历史,触摸历史就需要很多这种感性的东西。
潇湘晨报:我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唐小兵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杨苡先生是以女性的视角讲述历史。您觉得杨苡先生在讲述时有明显的性别视角吗?
余斌:唐小兵的这篇文章我看过,但是我现在记不住他具体的上下文,不太清楚他说的女性视角是什么。我在后记里面也讲了,是不是女性的视角,我不好说,但是杨先生的记忆有她的特点,我说她是抓小放大型。通常人们认为是大的事情在她那儿可能一笔带过,或者说她印象不深。我讲的抓小放大,不是说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力是抓大放小,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过滤是受到某种规训的。比如说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跟你讲的事情,可能和我写进书里的同一件事,就不一样。所以,这有没有性别记忆的差别,还是有另外的原因,例如我们无形当中受到的一种规训,关于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无价值,什么是大,什么是小的,可能也有关系。
当然杨先生的记忆有个特点,她的记忆相当场景化。我曾经打过比方,说如果去一个地方,她可能不大会记住门牌号码,但她能记住门口有一棵树,记住当时有一个戴什么帽子的人正好从这儿过,这些她记得很清楚。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些点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希望能够定格并且放大这些特征。
我在整理口述的时候就很有信心,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它的趣味和它的意义是一致的,是能够叠加的。同样一个事情,你可以认为是八卦,也可以说它是有价值的,关键是你怎么去看待它。有的事情可以是一种花边新闻式的处理,狗仔队似的处理,也可以有另外的处理。它里面众多的细节,确实有趣味性,同时我又希望我的处理不像过去小报上那种花边新闻。作为撰写者,我的愿望是这样的。
潇湘晨报:您在后记里面说到,作为记述者,您不是作壁上观的态度,也不是完全的局外人。
余斌:对,因为是口述史,我觉得作为撰写人应该把自己的痕迹抹去,最好是一个透明的存在。他的存在应该是以另外的方式,例如剪裁等等,要让人感觉到他不是介于读者和讲述者之间的什么东西。我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现场感:一个是口述者讲述时,例如杨先生讲述时,就像她回到了她讲述的中西学校、回到西南联大、回到她小时候的家;另一个是读者看口述实录时,也感觉自己就在那个现场,看到了杨先生的表情和语气,她虽然没讲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希望看到她的叙述时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潇湘晨报:杨先生那么坦然地把家族中不那么光彩、甚至是丑的事情说出来而且准许您记录,跟巴金先生的影响有没有一些关系?
余斌:影响很大。我觉得杨先生的认知框架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这个认知框架有很多是“五四”那个时候(的一些思想)给她的,那些在当时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一些东西,当时的青年大都接受的东西,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巴金那。巴金对那时年轻人的感召力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巴金说要冲出大家庭的罗网就想冲出,至于冲出后是什么,其实是很模糊的。所以,那个时候有年轻人是揣着巴金的《家》到延安去的。杨先生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延安对他们来说,就是诗与远方中的远方。
我告诉你msdn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作者已申请原创保护,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事宜、对本内容有异议或投诉,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